离婚周年祭:当讲台成为我的避难所

粉笔灰在晨光里飘浮的样子,像极了我去年签字时抖落的橡皮屑。
今天是我离婚整一周年的日子。办公室的台历用红笔圈着这个日期,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哭脸——是上周值日时,班上的调皮鬼陈浩偷偷画的。你看,连孩子都比成年人更擅长直面悲伤。
第一节课是初三(2)班的作文讲评。当投影仪亮起学生习作《家》的标题时,我的手指微不可察地颤了一下。这些十五六岁的少年永远想不到,他们笔下"像冬日暖炉"的家庭,此刻正刺痛着某个成年人的旧伤。
"王老师,您觉得真正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?"扎马尾的课代表突然举手。全班四十双眼睛望过来,我在那些清澈的瞳孔里看见自己陡然苍白的倒影。
一、职业面具下的溃堤时刻
教师休息室的热水器又坏了。捧着保温杯接水时,听见隔壁班李老师在抱怨丈夫不做家务。那些曾经让我烦躁的婚姻琐事,此刻竟成了奢侈的烦恼。
离婚后的第三个月,我在监考时发现有个女生在偷偷抹眼泪。后来才知道她父母正在闹离婚。当她在放学后拦着我问"老师,离婚会遗传吗"时,我差点把备课本捏出水来。教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保持专业,可谁来教我们缝合自己的伤口?

二、讲台成为我的情感教室
教师公寓的阳台上,前妻养的多肉全都枯死了。就像我们的婚姻,缺的不是水分,而是共同守望的耐心。但很奇怪,当我站在讲台讲解《诗经·氓》时,突然读懂了"言笑晏晏"背后的预警——有些悲剧早在甜蜜期就埋下了伏笔。
上周批改日记,看到班长写:"王老师最近上课总爱举婚姻的例子。"这个观察让我惊觉,原来伤痛正在不自觉转化为教学素材。那些深夜独自吞咽的苦涩,最终成了分析《红楼梦》家庭伦理时的生动案例。
三、在身份夹缝中重建自我
教师节收到的贺卡在抽屉里垒了厚厚一叠,落款都是"爸爸妈妈说谢谢您"。这些来自完整家庭的感激,像一面面镜子照出我的残缺。但昨天毕业的学生回校,说"您教我们《致橡树》时说独立比依附更重要",我才惊觉那些自我安慰的说教,原来真的能滋养年轻的生命。
现在批改作文遇到"我的家庭"这类题目,我会在评语里多写一句:"描写很生动,但记住,家的形式有很多种。"这话是说给学生,更是说给那个在结婚照前发呆的自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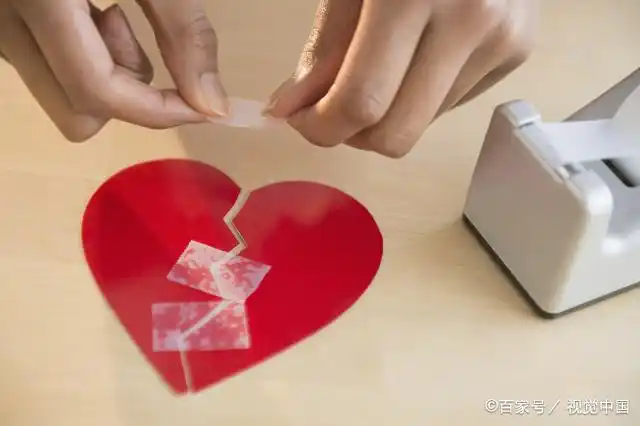
放学铃响起时,粉笔灰已经落定。就像这一年的眼泪,终于学会了在备课笔记上风干。明天早上,我依然会站在讲台说"同学们好",而那个藏在教案夹里的离婚证,终将成为批注在人生边页的铅笔字——可以被擦淡,却再不能改写故事的走向。
暂无评论